一颗初心,33年坚守
文章来源:《中国电建》官网2021年6月3日《重点报道》
我很现实,也爱幻想。踏进医院大门,因为所学专业,我做了各种各样的憧憬,对未来的设想既大胆又执着,这大概是年轻人的“通病”。
被安排到科室后,心头一阵窃喜,因为离梦想又近了一步,虽然那个梦想当时遥不可及,但至少眼前已经踩在起跑线上。
上世纪80年代中叶,产房、待产室、抢救室界限真的分得不是太清。在产妇宫缩的间歇,在胎心监护的间隔期,在滴催产素的观察过程,那些专业书籍夹杂在或哭、或笑、或无理取闹的“装台”上,慰籍了漫漫医路的寂寞,也填补了书到用时方恨少的些许空白,只是依旧杯水车薪。
产程图上不规则折线的累累擦痕,手术衣上时时被羊水、胎粪、血液的“浓墨重彩”,耳边不留情面的苛刻教诲,都没能终止我所谓破茧成蝶前的痛苦挣扎,打乱我做“梦”的步伐。因为,能力越强,白大衣穿在身上才越显得合身自然,技术越好,行走在医院里才会越发从容淡定,这是我从杨枝华、翁如兰两个主任那里得到的深刻验证。简简单单的白大衣,穿出高调奢华,穿出雍容大气,穿出学富五车。暗自思忖:白大褂穿在我身上,不能仅仅是一件工作服而已,因为它左上方,赫然印刷有黄河医院的名字!
生活就是这样,收获未必就能配得上付出,那些深一脚浅一脚的执念随着工作变动,憧憬也跟着移位。医疗界高级别的桂冠在我职业生涯于“医师”初级坐标处戛然止步。那个戴着光环的幻想就此脱离现实的轨道。
工作内容变了,职责范围转移了,悻悻地走进了当年刚刚独立出的医务科。还好,离临床就差一个三班倒,我依然穿着白大衣,保不齐哪天我又欣欣然挂上了听诊器,看着胸前魏碑体的“黄河医院”字样,咬咬牙,壮志又塞满了胸腔。
穿着它,生平第一次和现任的急诊科护士长参加了十一局《计划生育知识大赛》;
穿着它,亦首次登台主持了医院首届“三基三严知识竞赛”;
穿着它,编写过《黄河医院实习人员五定一转管理程序》获局级科技进步奖;
穿着它,参与《医院感染预防与管理》一书的编辑与校对;
穿着它,完成了《医院服务新举措—电话医生》论文的发表。
在日月轮回和斗转星移中,白色成了自己服饰的主色系,我明白,白色它不代表常人所谓的苍白,它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蜕变后的精灵。上班一穿上白大衣即完成家庭与职业角色转换的重要步骤,贴上白衣天使的标签。奇怪的是只要一穿上它就满血复活,精神抖擞,8小时内寸不离身。
或许是出于对老一辈医务人员名声鹊起的向往,穿着白大衣和他们并肩工作似乎更清楚方向、更全神贯注,还有一种被他们光芒折射的幸运,幼稚的我偶尔也会沾沾自喜和外人道“我曾经跟着卢涵辉、宫淑莲实习过两个月”,“得到过高立章主任的真传。”
“这件衣服不是谁都能穿得起的,你进医院穿上它,就得对得起它,它是职业,它是责任,它是黄河医院的代名词啊”。这是和縢(津浦)老1995年那个炎热的夏季一起编纂黄河医院院志时,在当年放疗科一间临时办公室聆听的教诲。
“上班就要有上班的样子,穿上白大衣,你就不能再像其他行业一样,因为你选择了一个与病人打交道的职业,而且都是在他们最脆弱和艰难的时候……”我不止一次的被梁治平老院长“洗脑”。
40周年院庆后,白大衣虽说还依然穿在身,终究是偏离了做医生的前行轨迹。这片偌大的森林里,一袭白羽的小小鸟却怎么飞也飞不高了。痛定思痛,我凝重地来回抚摸身上的白大衣和胸卡,再次看看胸卡上的科室和职称,走下了医师职称递增的道路。
DOS系统、用友软件、人工成本的财务传递、劳动合同签订、工资与劳动合同的人机共管、三项制度改革……一大堆的陌生名词,目不暇接,眼花缭乱,当然还是在医院。只要还能穿着白大衣,在哪儿的岗位我一样让它洁折光亮,不玷污渍,这是做人的底线,我爱白大衣,视它如生命。
从“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”“救死扶伤,患者至上”“医德奠基 科技兴院”“传承大禹 奋进不息”再到“科技兴院,质量为本”,医院的办院理念逐级加码,只有白大衣我行我“素”,我一路追逐,心无旁鹜把它穿成了“家”规;
它呢,上世纪80年代宽如裙裾,90年代长身过膝,现在又束腰塑身,或长或宽、或修身或简短,它纯洁如玉的本质始终如一,我如影随形,一往情深把它穿成了“家”风;
从业近33年,那个衣袂飘飘白衣胜雪的我,已两鬓微霜,和着流水月华,已然融为一体,虽不济同道们的术业专攻、才冠三梁,但和他们一道“群策群力,创造满意 ”共同守护白衣圣洁,义无反顾把它穿出了“家”训;
从最初第一件排号的356,到457、469、688,到目前的3021,像我的人生一样,一步步伴随年轮递增,再慢慢从人生的舞台上隐退。3021应该是最后一个“番号”罢。心思千百遍,我待你如初恋。我本想在职业生涯倒计时的日子里,自私一回,拿上你珍藏,时时眷恋一番激情岁月的难忘时光。现在想来大可不必,你朴实无华、从善如流的容颜已深入心岛。我穿或不穿,你都在我的身上。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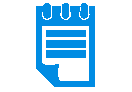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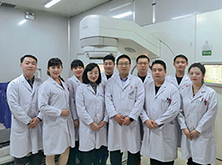
 豫公网安备 41120202000002号
豫公网安备 41120202000002号